沒有美圖秀秀的年代,肖像畫是一件神圣的事情
今天流行的selfie,磨皮濾鏡裝傻賣萌,這是社交網絡孕育的現代審美,且不論好壞,僅供娛樂也不錯。
但們不妨暫時將目光從這些美圖和秀秀上挪開,看看從前那些面無表情、呆若木雞的照片和肖像畫,他們的審美是什么?
還有那些將家庭的顯赫與美滿凝固成永恒,裝裱在高墻上的家族肖像畫,從歷史的望遠鏡里往回看,究竟是留給子孫瞻仰的,還是留給美術館的游客欣賞的?
這些,就從大都會二樓三對大有來頭的夫妻肖像畫開始講起。
鄭 重 其 事 的 肖 像
局部第二季 | 第十三集
講述 | 陳丹青
現代人拍照太容易了,用不著攝影師,也用不著攝影機,隨時拍,隨時轉發,手機里呢,還藏著各種美顏的軟件,喜歡自個兒拍。
去年我給一位粉絲不由分說就拉著合影,拍完一看,我的臉就成了一個剝了殼的茶葉蛋。
現在的彩色婚紗照,我以為很難看,好看的是黑白婚紗照,那種好看有一個神秘的理由,就是黑白,還有一個更具體的理由,就是,鄭重其事。
照相館的時代過去了,大家看得出來,早期攝影里的人物大多數是發呆的、嚴肅的,因為曝光太慢了,拍照人、被拍的人,個個鄭重其事。
百年上千年前,畫張肖像畫,非常非常麻煩,非常非常鄭重其事,換句話說,那是一件神圣的事情。
肖像這事,關乎臉面
埃及開羅附近出土的法尤姆肖像,距今有一千九百年,可能是人類早的肖像畫,不是人物畫,就是畫一張臉,肖像畫。
你看了會有點害怕,因為畫中每個人都目光灼灼,它不是畫完了給你掛那兒欣賞的,是將來要隨主人放進墳墓里去。
可是這樣的畫,連像倫勃朗、委拉士開茲這樣的肖像巨匠也無法超越,為什么呢?
古人做事啊,年代越是早古,越是神乎其神,越是鄭重其事,何況這件事涉及人類自己的臉。
《局部》季說過,古代的作品絕大部分都是訂件,沒有自由創作這回事兒,貴族的肖像,照本雅明說,就是權力和財富的證明書。
這是馬克思的觀點,對不對呢,很有道理的,因為窮人、老百姓哪有資格為自己畫肖像。
英國那位亨利八世,沒兒子,就一個接一個找對象,各國的皇家女就紛紛應聘,請人畫了精細的肖像送過去,給他選,誰畫呢?其中就有非常著名的德國畫家霍爾拜因。
法尤姆肖像的話題太大了,以后有機會另講,今天咱們看看二樓三對夫妻肖像,作者都是大腕兒。
安格爾畫皇親國戚
我們先從年代晚的開始,這是安格爾為一對貴族夫婦畫的像。
大家可能知道,安格爾和德拉克羅瓦公開叫板。德拉克羅瓦要走向浪漫主義,安格爾呢,要回到拉斐爾。
現在這倆冤家的畫掛在同一間房間里,大家自己做主,喜歡安格爾呢,還是喜歡德拉克羅瓦?
刻意古典的安格爾為了追尋他心目中的拉斐爾,成了個變形的畫家,女子身形的傾斜度、彎曲度被他悄悄地改變了、扭曲了。
現在墻上掛的是他為《大宮女》畫的單色草稿,過分修長的女裸體背部曾經引起很多爭議和考證,說是脊椎和尾椎骨究竟有多少節。
不管多少節,輪到為富豪畫肖像,又要美化,又要畫得像,安格爾就收斂了他的變形。
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辦過安格爾巨大的肖像回顧展,我去看了,每張都很厲害。
要論肖像畫的經典性,他可能是后一位極度認真的訂件畫家。
自古皇親國戚的肖像有一大看點,就是盛裝,安格爾描繪盛裝的時候,完全忘了拉斐爾。
我們來看這幅畫的下端,絲絲入扣,瑰麗而沉默。
他描繪的圖案,他的圖案描繪,半自覺地進入了現代的形式感,沒有宗教意識,也沒有人文主義。
有本畫冊叫做《安格爾與面料》,其中有很多安格爾繪畫盛裝局部的圖像,非常好看。
大家知道面料是服務貴族的一大行業,如今的富豪為他們的豪宅做裝修,窗簾啊、沙發啊、靠墊啊種種,都是從英法德意這些高檔的、祖傳的面料企業進貨,如今歐洲不景氣,蕭條了,真是可憐,許多這類行業都面臨生意短缺,甚至破產。
我在北京的居住小區對面,有一家福建人開的面料店,老板就很自豪地告訴我,他的下一步就是收購意大利祖傳的那種高級面料企業。
哈爾斯畫企業家
好,我們再來看我身后兩幅很小的圓形的肖像,誰畫的呢,是我喜歡的哈爾斯。
《局部(季)》的第七集吧,好像講過,哈爾斯是十六世紀阿姆斯特丹畫家行業公會的會員,訂件肖像大王,一輩子不知道畫過多少殷實人家的爺爺、奶奶、兒子、孫子。
這是我見過他的訂件肖像里格外精美的一對,處處手到擒來,簡直是在方寸之間炫技,可是又透著荷蘭繪畫的樸素感。畫中的這對夫妻,就是當時阿姆斯特丹辛勤致富的企業家。
歐洲在十六七世紀流行過一種非常小的、圓形的、畫在鐵板上的肖像,畫完以后就配上小鏡框,配上小金鏈子,就揣在懷里。
當時的荷蘭人,就跟咱們現在福建人溫州人一樣,經常跨海做生意,出門久了,想念家人,就取出來看一下。
大家看我手里面這兩個圓形的、小的、鐵板上的肖像,畫中人呢,我相信是當時的小少爺。
當然,畫功、境界,沒法兒跟哈爾斯比,所以哈爾斯的畫就進了博物館,這兩個小肖像呢,就歸我所有。
可是呢,你仔細看這些畫,這畫功了得,說明什么呢?說明當時歐洲有很多這樣的工匠,在為企業家服務。
梅姆林畫信徒
好了,我們后來看看十五世紀的德國畫家梅姆林。
文藝復興時期南歐、北歐的繪畫,那是各有各的厲害,過去荷蘭和比利時屬于一個地區,叫做尼德蘭地區。
尼德蘭繪畫單是出了凡·艾克和梅姆林這樣的天才,就能光照千秋。
這一對小型油畫肖像,我認為是北歐繪畫的珠玉之作,面對珠玉之作,語言實在是沒有用。
我們三對夫妻像看下來,我以為這一對神妙,簡直是超凡入圣,結果是超圣入凡,我想說,這也是梅姆林對他自己偉大規范的一時偏離。
十五世紀南北歐繪畫的主旋律,當然還是圣經畫,所以梅姆林作為副業畫肖像的時候,他的眼光、他的意識,就好像解放了,出現活人的真氣。
這對夫婦是意大利佛羅倫薩駐比利時的銀行家,等于是今天跨國金融界人士,當然,他們是信徒。
當時的歐洲肖像畫有一種通用的形式,就是三聯畫,中間是一個圣經圖像,左右呢,就是夫妻,雙手合十,虔敬地禮拜,年代一久呢,當中的圣經畫就遺失了,剩下左右這對夫婦,倒也成全了肖像畫的主題。
說來罪過,我也買到過一件十五世紀比利時的三聯肖像畫,也是當中的圣經圖像不見了,所以價格便宜。
大家看,左邊是父子,右邊是母女。
敦煌的卷子里頭很多也畫滿了左右跪倒的供養人,那另是一種好看。
但因為是年代太早了,一千多年前,用筆簡單,造型也雷同,不像十五世紀比利時這些家族肖像,神形畢肖。此外說明什么呢?說明當時的歐洲布滿家族肖像這個行業。
所以我每次看到(梅姆林)這一對肖像總是無可奈何。二十世紀攝影起來以后,像這樣子鄭重其事的肖像沒有必要了,也不可能再有了。
總是被子孫賣出去的家族肖像
現存的家族肖像,多半是在明清兩代留下來的朝廷命官、巨家富賈,祖孫滿堂、畢恭畢敬。
可是在明清啊,主流是文人畫,這些家族肖像進不了美術史,也進不了美術館。
?問題來了,俗話說,富不過三代,戰爭、遷徙、時代變故、家庭淪亡,歐美的古董店至今還掛著不少從來的明清的家族肖像,顯然掛了很久,不知道誰會買。
人是要拜祖宗的,祖孫三代的畫像怎么會離開祖屋,流到歐美呢?
樣的問題是,大都會收藏的這三對夫妻肖像,當初畫完了交貨,必定也是鄭重其事,可是家族背后的故事沒有人知道,也沒有人在乎了。
尼德蘭這兩份殷實的家庭,是到第幾代出手變賣了祖宗的肖像?
有趣的是,安格爾這對貴族夫妻的肖像不是為家庭后代收藏,而是被“印象派”大佬德加收藏了。
德崇拜“我主”安格爾,年輕時候拜訪過他。安格爾生于1780年,德加生于1834年,兩個人相差五十四歲,等于是祖孫輩。
了德加的時代,這對貴族夫婦可就離開了富貴之家,流入市場了。德加是一個狂熱的收藏者,藏品愈千,他死后,遺物拍賣,這對肖像就被美國人買了,日后捐給了大都會藝術博物館。
在說,所有古代肖像當初都屬于某個家族,都被族親后代賣了出來,永遠離開老家,進入美術館,供世人欣賞。
我們想想看吧,我們今天的億萬張家庭照片,億萬張夫妻照片,再過多少百年,還會不會有人愿意一遍一遍地觀賞?
木心說過,年代更替,藝術的重價值會自行消褪,進入第二重價值。
什么價值呢,藝術的價值。
-
18846121222哈爾濱移動¥4600查看詳情
-
13605847116寧波移動¥3250查看詳情
-
18558885111福州聯通¥5100查看詳情
-
15732515151唐山移動¥4600查看詳情
-
17884002345哈爾濱移動¥7600查看詳情
-
17832988881唐山移動¥5600查看詳情
-
13933413993唐山移動¥4000查看詳情
-
18820999998深圳移動¥4.80萬查看詳情
-
18788860222合肥移動¥7400查看詳情
-
15118500009東莞移動¥3436查看詳情
-
13956970555合肥移動¥7400查看詳情
-
13729999699東莞移動¥1.88萬查看詳情
-
13363235999唐山電信¥1.69萬查看詳情
-
13889916288深圳移動¥1.81萬查看詳情
-
18746144666哈爾濱移動¥6000查看詳情
-
15233250009唐山移動¥3150查看詳情
-
18332606000唐山移動¥6100查看詳情
-
15233396543唐山移動¥4100查看詳情
-
18304558885哈爾濱移動¥6000查看詳情
-
15820800003東莞移動¥3436查看詳情
-
13865990555合肥移動¥7400查看詳情
-
18304558887哈爾濱移動¥6000查看詳情
-
18346244666哈爾濱移動¥6000查看詳情
-
13788888164福州移動¥3150查看詳情
-
18597777997福州聯通¥3150查看詳情
-
13865927555合肥移動¥7400查看詳情
-
18811887798深圳移動¥6700查看詳情
-
18558889222福州聯通¥4600查看詳情
-
13905910199福州移動¥3150查看詳情
-
13933499313唐山移動¥3.85萬查看詳情
-
13703661119哈爾濱移動¥3688查看詳情
-
17759094444福州電信¥3150查看詳情
-
13733333726唐山移動¥6500查看詳情
-
15530829000唐山聯通¥6400查看詳情
-
13966377388巢湖移動¥4000查看詳情
-
15280000099福州移動¥3800查看詳情
-
18597777736福州聯通¥4600查看詳情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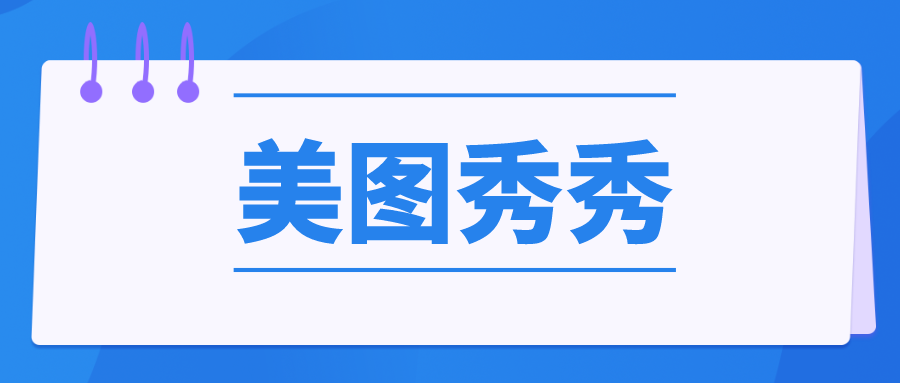
 手機號碼估價
手機號碼估價 號碼歸屬地查詢
號碼歸屬地查詢 手機號段查詢
手機號段查詢 區號查詢
區號查詢





